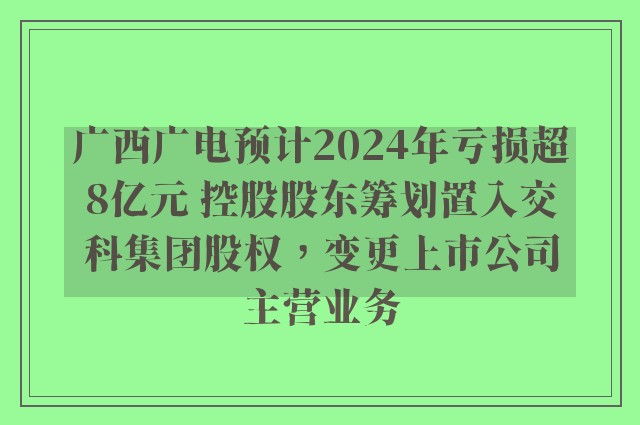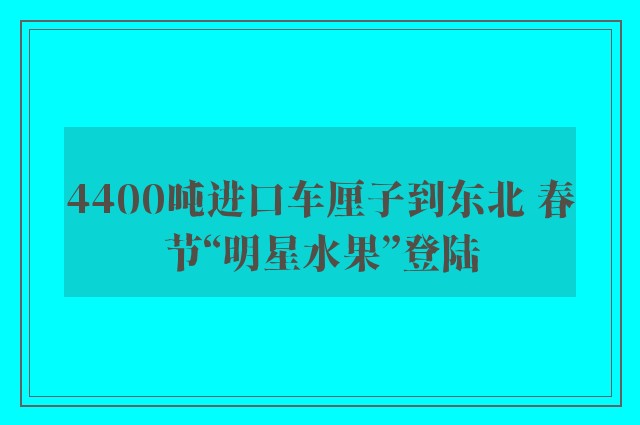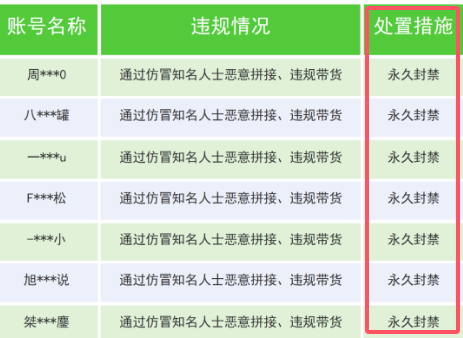说不清故乡的规划师,为何要漫游小地方和城市的角落?
离2025年春节还有不到两个月,已经有很多人抢好了返程机票,在盘算过年带什么礼物回去给父母家人。从大城市回到小地方,Mary、Alice、Olivia将变回丽丽、小红、阿花。住在北京的城市规划师、“85后”专栏作家李昊可能会回郑州和父母一起过年,也许他新出版的书《小地方》会成为带给父母的“年货”之一。
但郑州这个前不久才上过热搜、有数万年轻人骑自行车跨城旅行的大城市,并不是李昊心目中真正的故乡。生长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快速膨胀年代的人们,跟他一样说不清归属地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一代人启程漫游,观察周遭,拿起笔来,写下的是不一样的感触。

《小地方:关于空间的漫游》
李昊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版
最早写鹤岗的人之一
鹤岗是这几年的全国级网红城市。11月下旬黑龙江大范围暴雪,鹤岗是降雪区之一,很多迁居的南方人把积雪巨厚的街景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
像鹤岗这样因工业下滑和人口流出而呈衰落之势的城市,被规划界称为“收缩城市”。学界、业界关注收缩城市由来已久,大大超前于社会舆论的关注时点。
2012年9月,《收缩的城市:第一卷 国际研究》一书出版,介绍了英国、比利时、芬兰、意大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等国家的收缩城市。2014年,中国学者们发起成立“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2019年7月,清华大学龙瀛研究员发起第一届中国收缩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坊,就在鹤岗举办。官方政策文件里,也第一次出现了“收缩城市”这个词。
李昊自称是“网上最早写鹤岗的人”之一。2019年秋冬之际,鹤岗“白菜价”卖房、南方年轻人购房迁居的新闻火爆全网。那年夏天,李昊以这个话题为契机写出《收缩城市vs一次逃离》并发布在“规划中国”微信公众号上。
“当时还没多少人关注鹤岗。我在百度‘隐居吧’看到舟山人李海发帖子《我存了五万,准备去鹤岗买房隐居》,我在文章结尾就写到他。这样的人,虽然既不崇高也不伟大,但值得被铭记。在时代大潮下,微观个体的自主选择,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李昊说。
这篇名为《一次逃离》的文章,收入《小地方》第四章《世间游》。李昊写道:“在这个时代,城市与人一样,都是成功学的信徒。那位鹤岗的隐居者,在世俗意义上也是一个逃避者或是失败者……但我却认为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它甚至有着积极的意义。”
“城市有成功、繁荣和不断扩张的权利,这是主流叙事里比较正确的方法。但它也有收缩、破败、退出城市竞争的权利。城市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个体意志的选择值得被尊重、被书写,收缩城市的悲剧美学也是有正向意义的。这样的城市是不是也有一些积极的形象,从外在功能到内在的文化精神上,也是值得探讨的。“李昊说。
在他看来,当前社会舆论从热衷于宏大叙事转向追求“小确幸”,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进入了“后快速增长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能不能更多元化地观察城市和人,用更加微观的、个体的、人文的视角,去看待不一样的选择?
他也到鹤岗去,为空旷的矿山公园、远山和散步的人拍下照片。他观察到大兴安岭的小镇,看到那里的年轻人们开展自给自足的生活实践,试着把小镇变成“北国的大理”。在最北的地级市黑河的冰雪中漫游,在俄式建筑和花园中展开北境的想象,感受“孩提时代曾向世界投以的一瞥”。
李昊也在更多的文章中写下不为人知的小地方的故事。在每个地方,他都试着过一段当地人的生活。在内蒙古二连浩特,他步行七八公里穿越地广人稀的城市,观察不同民族联姻的家庭聊天。在边境不知名的小镇的老市场里,他寻找大城市里已经很少见的裁缝摊,缝补衣服和背包的扣子。在十堰市区北边的老城郧阳,他游走在丹江口水库淹没老县城之后建起的新城,看生态移民怎样在崭新的社区里生活。在水电站大坝上,他感叹,有没有市民在这宏伟的景点,趁着夜色跳广场舞?
大流动的孩子
和改革开放后出生、千禧年后上大学的这代人一样,李昊的生活、工作都处在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大潮之中。他出生在豫南驻马店市下属一个县的村子里,却没怎么去过驻马店市区。小时候他常去奶奶家,那个村子距离漯河市区更近,经常要去漯河坐火车。
4岁到12岁,他随父亲在新乡市郊的一座部队大院生活,那里被他视为真正的故乡,但大院悬浮在主城区之外,像一个孤岛。父亲南下深圳干工程,暑假时他跟母亲一起去团聚,黄土抛天、工资高消费也高的特区给他留下印象。小学六年级,他们一家搬到了郑州,李昊花了一年时间才融入那里。
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李昊在美国、欧洲求学和旅行。在葡萄牙当沙发客的时候,房主说,按惯例,每一位来访者要写下自己的家乡,精确到村。李昊说,我可以把村庄的名字写下来,但我很难说我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之后很多年,李昊在北京的大型城市规划设计院工作,经常飞来飞去,调研各种各样的城市、小镇、村庄,研究各个地方的发展,为政府编制规划。他喜欢在途中从小处着眼,记下每个地方的微观故事。2019年出版的《城归何处:一名城市规划师的笔记》一书,汇集了李昊作为爱写作的规划师对中国城市现状的思考文字,当时他已经为十多家媒体供稿,成为“最会写城市的规划师”。
“有一天有一个读者联系我,他说他为了准备考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生,买了我的书,读后觉得被骗了:发现这不是一本专业书,里面怎么写了这么多天马行空的东西。”但当时《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采访李昊,却告诉他:“像书中第三部分《乡愁与城愁》这样,把这些中国城市的状态写得如此生动,从来没有过。”
李昊决定,下一本书他将不再写那么多城市规划理论知识,要为和自己一样喜欢从细节认知城市、热爱旅行的读者写作。在《小地方》里,他写了更多名气不大的“小地方”和大城市里常被忽视但却有趣的角落。
他不按流行方式旅行,喜欢在漫游中搜罗各地的细节,但城市规划专业还是为李昊的文学书写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几年我看了很多旅行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书籍,觉得许多书有着类似的套路:每到一地,总是仅仅通过采访当地人来记录这个地方,笔墨全部集中在人的故事上,地方环境只是一个易被忽略的、简单的背景。其实人的特质和大地是充满互动、相互塑造的,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相当浓度的恋地情结。写出地方感与空间感,是我想要提供给大家的一种新视角。”
写童年迁居史,他记录下从幼时就开始感受到的中国城市化三十余年经历的种种变化。写回村为奶奶送葬,他观察到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新农村建设。写成都,他在“新一线城市”崛起路径中谈论造新城与留住烟火气的关系,并敏锐地观察到说唱亚文化在其中的意义。写浙南不断工业化的村落,他谈的是乡村工业化与何处安放乡愁的矛盾。写北京的回龙观、鼓楼大街,他写的是背井离乡的“小镇青年”们需要的社区服务和适合约会相亲时漫步的街道。
“看似琐碎、跳跃的‘小地方’的视角,真的能理解这个世界吗?”李昊说,“当然,只有真正走进‘小地方’,才能够于孔隙之中发现旷野。”
对话李昊:中国城市确实“千城一面”,
所以更需要沉下去,在细枝末节处挖掘它们的特点
在《小地方:关于空间的漫游》中,城市规划师出身的李昊发挥了从小爱浮想联翩的特点,把大量文艺元素和成长回忆,融入在城市、乡村与荒野的漫游当中。他的写作是对城市书写方式的新探索。回忆及思考城市规划师工作轨迹之余,李昊对第一财经分享了阅读、漫游、写作过程中的思考。
感知小地方,寻找真挚情感
第一财经:很少有城市规划师给大众读者写城市。你为什么这么做?
李昊:我从小喜欢地理和地图,长大以后喜欢旅行,在各地有很多见闻。做城市规划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很多想法,想利用业余写作的机会跟大家交流。上一本书《城归何处:一名城市规划师的笔记》有一定的专业性,新书的定位就是要跳出行业的专业性,但也保持了空间的观察视角。
段义孚说“地方”是人与环境通过情感联系形成的产物。项飙则把人与人的连接称为“日常自我价值的微观构造”。我想基于人与大地的情感,为旅行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提供一种新的、更加多元化的视角。
《小地方》关注非传统、非主流的细节,在宏大叙事的典型性之外,寻找被忽视的日常生活、被边缘化的地方——那些生命体验中的“沉默的大多数”。因此这本书既有大都市的细节,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乡村和偏远的荒野。事实上,对于在主流叙事和网红打卡之外的景观的探寻,也恰恰是对自我内在丰富性的挖掘。

《城归何处:一名城市规划师的笔记》
李昊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年11月
第一财经:城市规划比较抽象,但城市是每个读者都感兴趣的话题。你写城市的方法,是怎样形成的?
李昊:上一本书出来之后,有个出版社编辑找我,想让我写一本新书,从城市规划视角谈国内各个城市,并将其定位为畅销书。我跟他说,以城市规划为视角的论著与畅销书生成的逻辑是不同的。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对象涉及人的日常生活,理论上应该很贴近大众。但其学理范式,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和专业性,与我们的直观感知有一定距离。这也是许多学科的特性:想要改造世界,首先需要从世界中抽象出来。具体的、跨界的交流沟通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笔下的空间漫游,一方面是向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段义孚的《恋地情结》等著作致敬,这些学者能够面向大众,用富有文学性的语言,以通俗但富有诗意的表述,产生专业之外的更大的影响力。这些著作让我深刻感受到“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另一方面,这本书也向很多文学作品学习,比如像托卡尔丘克的《云游》、杰夫·戴尔的《白沙》那样结合了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那样的“地志学书写”,以及保罗·索鲁和简·莫里斯充满敏锐“触角”的旅行文学。
把游记、散文、艺术、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等视角融合在一起,尝试在漫游中感知地方的细节,挖掘其中的情感,再用散文叙述缝合。通过这种写作,我尝试探寻那些难以言喻的、在人与大地的互动中感知到的生命经验。
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困境,许多非虚构写作喜欢探讨这种话题,它们直面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却把地方环境作为一种模糊的背景。事实上,我们对地方的感知和想象,也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疫情几年,旅行受到一定限制,只能深深潜入日常生活和寻常之地,探寻地方的丰富性。当你走向“小地方”,你其实是走向了世界。
回忆漫游,也是一道风景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写到那么多歌曲、电视剧和书籍,还把它们跟年代和城市发展问题关联起来?
李昊:我从小喜欢浮想联翩,特别喜欢在看似无意义的细枝末节上进行无限的扩张和展开。每到一个地方,脑海中就开始天马行空。我刚刚看了贾樟柯的新片《风流一代》,是一部很有时代性的电影。特别是影片前半部分,可谓是深深镌刻着时代烙印的影像集。我想我可能跟他的表述挺有相通性的,我尝试将游走时的感触,关联到脑海里曾经有过的文艺作品,形成一种拼贴式的客观记录。文章中许多看似琐碎、漫漶的内容,共同编织出一种超越表象的观念与情绪之流。在我看来,这是表达人地情感的一种方式,就像简·莫里斯的说法,对不同的地方“迷恋,又失恋”的感觉。

第一财经:我们“80后”这一代,作为改革开放之后赶上快速城镇化的几代人之一,享受到了某种观看的权利。感受特别多,也在变化当中积攒了很多人生素材。这种变动性对你的影响怎么样?
李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大时代的积累作用于微观个体。还记得刚考上大学时,我特别不想去读,不喜欢工科学校的氛围。后来和爸妈一起去学校,住到宿舍里,我突然朦朦胧胧感觉到,我家这一辈从农村到城市,大的人口迁移和城乡巨变对我内心深处产生了潜移默化又深远的影响。我的世界观形成和人生选择,在冥冥之中有隐形的大手将其左右。
对于我们80、90后来说,大多数人都成长于人口大流动的时代,空间上的迁移和漂泊通过代际文化心理的传导,对人的塑造、对人对地方的感知和理解,都有很大影响。按照美国诗人路易丝·格丽克的说法:“我们只看过这世界一眼——在童年之时,剩下的都是回忆。”很多时候成年人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与享受的快乐,未必能与童年时探索家附近小径的幸福感相比拟。我在各地的漫游中也在寻找童年记忆和感受。在沈阳铁西区和北京复兴路的大院地带,童年在部队大院的经历浮现在心头,这些地方勾起了我强烈的回忆。
我爸妈那一辈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他们辗转了几个城市,这个过程对我的影响很大。《小地方》里有一篇长文《奶奶》,写的是我回村送葬的事情,也写到父母辈脱离了农村,但还保持着农村社会的思维方式,作为家族在城市的第一代移民,有过许多漂泊的经历。我还写到回龙观,当时我租房子的房东属于第一代移到北京的人,带着小孩从东北小城市来北京奋斗。她在奋斗过程中形成的强势风格,就对孩子的性格有一些影响。
城市与家园的微妙显影
第一财经:《奶奶》这篇文章里你写到同村的乡亲跟你说“你回来把老家好好规划规划”。你在农村的亲戚对城市规划的认知,是希望你报效家乡,把老家建设好,特别朴素也很有趣。但你也写到在周边县做项目不顺利。很少有规划师谈这个话题,你觉得你做这行能建设好家乡吗?
李昊: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乡亲们以为我能报效家乡,把家乡建设得更好,但是我跟他说,我在隔壁县做了规划,有些内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规划要将许多村庄合并到中心社区里,农民离开村庄,搬家住楼房。这样的方式当然有些激进,背后涉及的原因很复杂。
在图纸和文本上,可能几万人、几十万人都只是空间布局所涉及的一个数字。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对每个人的搬迁来说,关乎的可能都是一生的生活。所以我当时感觉很难对同村发小的发问作出回答,他会是一个大数字的多少分之一吗?
这件事也涉及我写作的一个思路来源,就是宏大叙事之下微观个体的感受。规划师置身事内,往往只谈宏大叙事。叙事背后关于个体的意义是什么,很少有人探讨。
刚工作的那几年,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如日中天。一些搞地产开发的朋友收入很高,但这也来自链条上的某个环节。高收入依赖于房价上涨,你从土地财政中分到一杯羹作为奖金,又拿着这笔钱去买不断涨价的商品房,为整个链条做了贡献。他们有时候搞一些超级大盘,甚至谋划建造一座新城,看似是在地图上布局一盘大棋,但自己也是小小的棋子之一。是不是有一种既悲壮又幽默的感觉?
第一财经:在《贵阳往事》这篇文章里,你写“爽爽的贵阳”有趣的地方。你虽然吃不惯折耳根,但还是写出了城市的质地。在网上,人们谈贵州总是谈到经济落后、地方债欠得多、地方资金链断裂等,都是不看好的声音。写这样的城市,你觉得与众不同的空间在哪儿?
李昊:贵阳是我出差驻场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不过触发我动笔的契机,是读到北京作家春树在网上写的一些游记,有一篇游记中突然蹦出来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的一些话。我当时就想,作家能用雅各布斯的话来注解她所理解的城市,我站在“造城市的人”的角度能不能从旅行文学的角度来记录城市?
所以我写的贵阳是基于微观视角,以一种文艺的方式去叙述外来个体对于这座城市方方面面的感知,而不是叙述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这些东西都是大的背景。小学时候我从杂志上看到一些关于贵州经济落后、贵阳暴力犯罪比较猖獗的报导。结果一去,发现环境体验很好,城市充满烟火气,让我印象很深刻。
中国城市确实很“千城一面”。在国内城市游走,很容易就能看到大部分城市无聊的一面。所以这就更需要沉下去,在细枝末节处挖掘城市的特点。比如“爽爽的贵阳”这句城市口号,很大众化,我估计是营销策划的行家想出来的。这种词让习惯了官方口号的人来构想,绝对没人能提得出。
第一财经:你觉得出差、旅游、说走就走等不同的“玩法”,对观察书写的影响是怎样的?
李昊:到一个地方,不管是因为什么机缘,我都比较喜欢一个人沉浸式地进入这个地方。太便捷、太安全,不利于全身心去感知陌生地方的冲击。
我写过一位外国建筑师,他坚持每到一个地方做项目,一定要先过一个星期当地人的生活,再开始工作。在北京,他专门整了辆自行车,我陪他从天安门一直往外骑,骑到五环外。
这种调研方式,可能很多专业工作者无法奢求。一个学者说他去过的全国所有城市,都是飞行开会,去了很多地方,但完全没深入了解各地,这些地方对他来说,永远是浮在空中的。这也挺遗憾,身体触达到了无限的空间,但思想和精神上依然是很局促的状态。
当下火爆的City Walk(城市漫步)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或本雅明素描过的巴黎城市漫游者。对我来说,最理想的漫游方式也是这样。1953年,居伊·德波、让-米歇尔·曼森在巴黎不间断地搭便车“漂移”,以一种看似混乱的漫游方式进行“日常生活革命”,反抗资本化的城市景观。我们可以将城市漫游者的生活观察方式,扩展到远方的小镇、乡村和荒野。我的文章也希望能带读者踏上心灵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