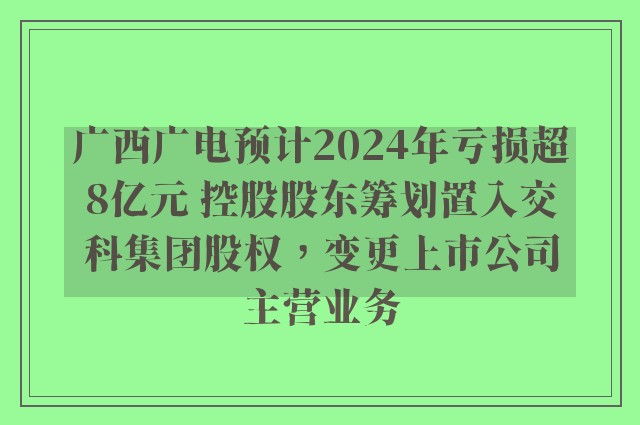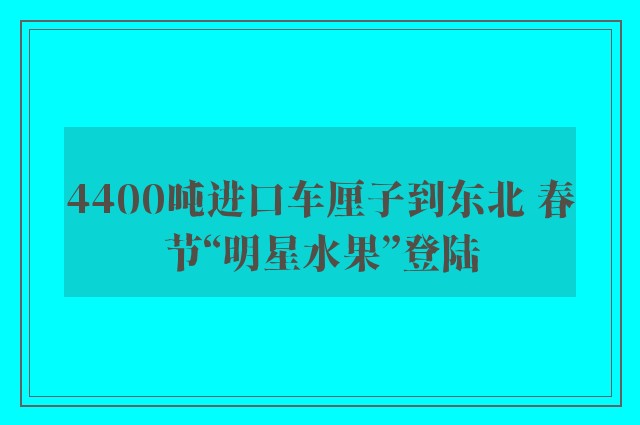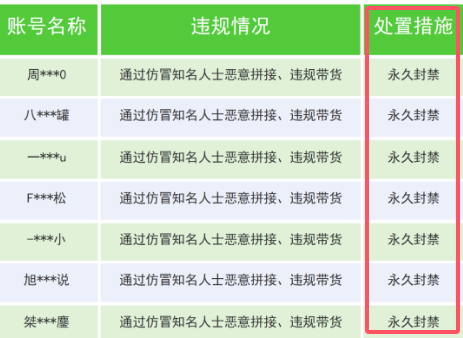当高学历女性决定生育二孩,身为母亲的困境与困惑
“生不生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几乎每个生了一孩的家庭都会遇到这样的“关心”。全面三孩政策公布后,二孩家庭普遍又会被“灵魂拷问”——要不要生“三孩”?
在中国社会,过去30多年里,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城市女性。她们普遍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经济条件,同时这些女性也是受“密集母职”影响最大的群体,一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努力平衡或者寻找解决方案。都说养育二孩困难重重,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使她们选择再次成为母亲呢?
2015年,也就是“单独二孩”实施两年后,尽管全国范围内生育率提升的效果不如政策预期,但陆陆续续还是有人开始生二胎。这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也陷入“生还是不生”的纠结,并对二孩问题产生好奇,开始研究“单独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2017年,蒋莱邀请刚刚回国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一起加入二孩妈妈研究。两位学者主要以上海为中心,对40余个家庭做了60多次深入访谈,从性别视角揭示了生育背后的母职困境,旨在反思两性角色与父母职差别,试图推动性别平等加速发展。
这些研究最后形成了新书《新生育时代》。

《新生育时代》
沈洋、蒋莱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2024年10月版
女性更决定是否生二孩
所谓“新生育时代”,是指如今的生育至少从生育背景到生育理由,都和以往有了明显不同。
说到计划生育,至今还有很多争议。但沈洋和蒋莱的研究发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周期里,只有在很小范围和有限条件下才等同于独生子女政策。受政策影响最大、实施“一孩制”最严格的家庭主要集中于城市、良好受教育背景、公有制单位、体面就业几个标签下的育龄女性。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二孩乃至多孩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也就是说,二孩话题,真正高度相关的政策目标只涉及很小一部分群体,“同时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这十余年陆陆续续放开的二孩政策效果始终远远低于预期”。
具体到书中的受访者,她们大多生活在上海,也有福建等地的少数女性,年龄集中在“70后”及“80后”,以二孩妈妈为主,也有少数三孩妈妈。这些女性的生育受政策影响很大,二孩或三孩都是相关政策出台后生的。
受访者以职业女性为主,55%的人是独生女,只有10%的丈夫学历高于妻子。这些女性能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同时,也离不开强大的代际支持和经济实力。就算是晚婚晚育,她们也踏准了时代的节点——毕业于中国GDP保持10%高增长的年代,基本在2010年前买好房,那时住房收入比值相对合理;上海也没有限购政策,他们婚后为了孩子教育又买了第二套或第三套房,完成很多后来人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超过15位被访者的家庭居住面积超过170平方米,1985年以后出生的被访者,普遍到结婚时父母已经准备好房产。
因此,这些女性的二孩生育理由也出现新面貌:“女性在生育二孩的决策中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问她们生二孩的原因时,最经常提到的理由就是两个孩子可以互相陪伴,没有一个二孩的被访者提到是因为自己的男孩偏好或者是养儿防老这样的理由,所以跟传统的生育理由已经很不一样了。”
当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时,还会出现“二孩跟谁姓”这样的新话题。受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一例是一孩随母姓。“冠姓权”发生改变背后,又涉及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女方在孙辈抚养上付出更多等家庭权力博弈,也有推动性别平等的因素。《新生育时代》分析说,在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当两个家庭为“冠姓权”做博弈或协商时,体现了家庭变迁的新变化,以及代际互动中“母系化”的倾向。“‘冠姓权’这个问题被看到、被提出,就是性别平等认知和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体现”。
所有人的母职困境都一样
不过,这些女性尽管经济条件和受教育情况都高于一般女性,在做母亲这个角色中面临的困境,其实和普通人没有太多区别。
由于受访者们普遍都是高学历女性,家庭里大到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以及孩子们入托入学、与老师们打交道,管孩子的作业、学业、兴趣班,基本上都是妈妈们在操心。“你可真是既主内,又主外!”这是和二孩妈妈们交流时,两位学者经常忍不住感叹的一句话。妈妈们还说,丈夫通常在生育了一孩之后投入不多,直到生育二孩后妻子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教育,他们的参与度才开始增加,很多家庭由此爆发各种矛盾。
出生于1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境优越的宋钰涵的经历就是典型。她结婚后三年内生了两个儿子,老二出生不久,她就做了全职妈妈。这时宋钰涵发现,丈夫还是保持着大学时的样子,每天可以花8个小时打游戏。“本来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丈夫什么都不搭手,我想生了第二个他总能长大一点,责任心更强一些吧,但是他进步没有那么明显,我就更累了”,“他什么决定都不做,只能我通知他”,宋钰涵觉得自己像“养了三个儿子”,“每天穿什么衣服还要我给他找”。有时晚上她陪大宝练琴,叫老公带着老二,“他所谓的看着孩子就是带着孩子打游戏”。宋钰涵不理解,为什么同时成为父母,丈夫却不愿意与她一同承担。

一旦成为母亲,她们普遍还面临“母职惩罚”。苏晓洁与丈夫齐越航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是名牌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同学。晓洁本科就在该校就读,丈夫还只是普通二本。毕业后,晓洁去了三甲医院做儿科医生,丈夫继续读医学博士,可以说,他们进入婚姻时的起点几乎相当。
孩子出生后,两人的职业发展出现明显分化。儿科医生工作辛苦,每周需要值夜班,晓洁在照顾女儿上有心无力,就跳槽去了外资药企,收入和医院差不多,不上夜班,但经常需要出差。二孩生下来后,晓洁再次跳槽,到社区医院儿保科室,这下上班非常规律,不用加班也不用出差了,但收入又少了足足三分之二。
就在晓洁两次为家庭做出工作变动和牺牲时,一直在三甲医院的齐越航凭借努力和钻研,事业发展却越来越好。他不仅读了博士后,还去美国、德国学习,年纪轻轻就当了学科专家和博士生导师,收入也跻身业界顶流。与此同时,晓洁也觉得丈夫身上“爹味”越来越浓,不仅对自己要求高,对身边人的要求也水涨船高。2017年,晓洁第一次接受沈洋和蒋莱访谈的重要因素,就是想吐槽一下他,“希望我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或者什么都完美”。
很多受访者告诉沈洋和蒋莱,“能够不出轨、多赚钱,扮演好家庭经济支柱角色,就是二孩妈妈眼里的合格丈夫”。而较早遭遇低生育率问题的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配偶参与度增加,女性的生育意愿才会有所提升。
女性学者“把自己作为方法”
这两年,随着中国生育出现新变化,国内不少学者也写过关于人口或者生育方面的书,比如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的《后人口转变》、企业家梁建章的《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等,但都是男性视角。作为国内首部从性别视角聚焦生育问题的著作,由两位女性学者联合完成的《新生育时代》,也践行了社会学上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在书中也坦诚写了很多自己作为独生女和母亲的经历,从而达到与受访者和读者的共情。
生于1979年的蒋莱从小就很优秀,大学毕业后获得通往更好学府的保研资格。对此,母亲显得“既得意又担忧”,“她既期待我事业有成,又担心高学历和事业心会吓退追求者;既谆谆告诫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又放不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民间规训;既怕我嫁不好,又怕我嫁不出去”。
婚后不久,蒋莱就意外怀孕了,还未来得及思考要不要成为母亲,身边的声音就都在鼓励她生下孩子,“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几乎无人问津”。
从2013年开始,随着国家对生育政策做出调整,蒋莱朋友圈中关于二孩话题的转发越来越多,家里类似讨论也变得密集。丈夫和8岁的儿子都想家里多一个孩子,但作为一孩都生得十分勉强的蒋莱,回顾儿子的成长路,“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操心,再来一遍光想想就令我不寒而栗”。
于是在2015年,她申请了“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走上“以学术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一年,蒋莱儿子小升初,从前的“乖宝宝”转眼成了青春期少年,一下变得叛逆。她想尽办法应对儿子“成长的烦恼”,甚至一度去求助心理咨询,生老二的念头自然也被彻底打消了。
作为更加年轻的学者,2017年,沈洋在婚礼上以《一份带有“女性主义”元素的婚礼发言稿》,在朋友圈“火”了一把。“作为女性主义者,你为什么要结婚?”沈洋在婚礼上说,这是很多朋友听到她婚讯后的第一反应,她因此要郑重解释“我为什么要结婚,以及为什么要和杨帆博士结婚”。当时沈洋说:“除了爱情和三观相符合之外,我们想用实际行动去构建一个性别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在中国,很多女性经历着‘丧偶式育儿’,很多家庭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杨帆重视家庭,愿意主动承担各种家务,喜欢买菜、做饭。他之前跟我说:‘如果生孩子的话,我没有办法替你分担,要让你受苦了,但是抚养的话我会尽力的。’所以无论大环境如何,我们希望能构建一个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
2019年,沈洋生了大女儿。杨帆也尽力遵守婚前的诺言,在育儿和家务上高度参与。两岁之前,他们家里也有育儿嫂,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他们的生活节奏,这时育儿嫂已经辞退,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又陷入长时间停课,夫妻俩还都有繁重的教学工作,家庭矛盾自然开始尖锐,“更多时间和精力被投入无偿劳动和争吵”。后来,他们赶紧重新找了一位育儿嫂,阿姨每天陪孩子读绘本、做游戏,“夫妻关系也大大缓和,基本没有再吵过架,不光有偿工作时间大幅增加,连个人休闲时间也增加了”。
“女人事业和休闲路上的绊脚石太多了,家庭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沈洋曾这样感叹。但在《新生育时代》的书稿快要完成时,沈洋怀二孩已近9个月。与很多受访者一样,这也是他们夫妻在权衡了经济、人生规划、工作状态等方面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虽然丈夫仍然给力,二孩也随她姓,但沈洋认为,看似其乐融融的背后仍然有很多难以言说的艰辛。“这使我想到,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不是幸福,也肯定不是没有压力的生活,更可能是一种体验,一种尽情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和心态”。
对话沈洋、蒋莱
社会轻视照料劳动,“奶爸”们也会遭遇和妈妈们一样的问题
社会科学中被忽视的母女关系
第一财经:《新生育时代》里说,国内有关母女关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非常少,看到这里我想了一下,发现确实这么方面的书很少。包括多数国产电视剧,都集中在说婆媳关系,母女关系这么重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蒋莱:国产家庭剧更多都关注婆媳关系,还是受传统父权制影响,认为女性婚后就要从夫居。电视剧都希望有个和谐的大结局,那“大和谐”不就是媳妇要依顺婆婆吗?尤其在很多非一线城市,传统观念还是默认孩子生下来就要婆婆带,所以婆媳关系也更受关注。其实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就想通过访谈,从社会学维度展示母女连接的真实状况,这也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表达。
沈洋:传统父权制下,女儿被认为总归是要嫁出去的,是“泼出去的水”。而且在传统社会,女性20岁左右就嫁出去,确实和婆婆生活时间也更长,很多文献都是歌颂母爱,不太关注母女之间的代际互动。
蒋莱:我们在书里也提到,东亚文化传统中的父权文化观里,母女两代人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在这个维度上母女是有共性的。母亲生出女儿,可能就比较失望,因为她期待男孩,也知道女儿会经历怎样一个性别歧视的一生。但是母亲也希望女儿过得好,就把一些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的要求强加给女儿,所以母女之间互相的关系很复杂,是大家说的“相爱相杀”。我们通过访谈梳理了这种母女关系。
高嘉萱和她的妈妈就很典型。高嘉萱妈妈很能干,又喜欢控制,是高嘉萱生活中最大的烦恼来源,母女俩经常互相顶。但是,高嘉萱妈妈既是时代的受害者,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她在多子女家庭长大,是不被重视的第三个女儿,初中毕业就随大流去了安徽插队十年,后来婚姻也很坎坷。
高妈妈作为单身妈妈回到上海后,从餐饮店服务员的顶替工作开始,到考会计证,转而坐办公室。这样能干的女性如果生活在现在,或者受到好的教育,就能发挥她的特长。但是她被时代局限了,只能在家里面做主,甚至发展成控制,在女儿择偶、找工作、教育下一代等方面都会去干涉,女儿也在人生每一件大事上都违抗了母亲,母女俩不时发生激烈争吵。
其实我们的研究一开始没有太关注母女关系,受访者大多围绕着城市身份、良好教育程度以及体面就业这几个标签。和高嘉萱交流时浮现出来的母女关系议题,让我和沈老师都被触动了,回望上一代妈妈的历程,细厘母女关系中的普遍与特殊、正常和反常,并进而探讨母女关系对新一代女性生育观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母职”概念的演进和认知发展。
“全职爸爸”与父职困境
第一财经:你们对“全职爸爸”的访谈,让人看到这些年家庭内部结构的新变化,网络上也有些全职爸爸大方分享自己的带娃生活。没想到的是,爸爸全职后一样会有“父职惩罚”。恰好前段时间我看了《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作者也讲到2010年前后,日本男性参与育儿后面临的困境,比如同样“既无法做家务,也无法育儿”,遭遇“男性育儿歧视”,“男性休育儿假遭受冷遇”,“奶爸”们的遭遇和妈妈们一样。为什么育儿角色变成爸爸,“惩罚”也随之而来?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蒋莱:这就说明,不管是“母职惩罚”还是“父职惩罚”,社会对照料劳动都非常轻视。其实照料劳动非常重要,不管是照料小孩还是老人,都是照料弱者。但把这些劳动回报放到市场上看,会发现社会认可非常现实。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保姆、钟点工、护工的工资不低。但是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家政工工资就不算高,中产家庭都请得起。而且育儿嫂和护工都是每个星期工作6天,工作时间24小时无休,他们普遍也没有社保,是很辛苦的。照料劳动的现实造成了职业性别隔离,大量照料劳动由女性来承担。
沈洋:在东亚三国中,日本的育儿保障更加全面。2020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要休育儿假。日本在法律上允许父母双方都休育儿假,但只有极少的男性使用这项权利,因为日本的文化传统还是“男主外、女主内”,小泉进次郎是日本第一个休育儿假的男性内阁大臣,其实就是向全国人民做出表率。
但是对雇主来说,员工因为照顾而请假就是影响工作,这会有一些收入或者晋升上的惩罚。因为雇主就是要求一个很忠心的、能更加投入的理想工人,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对家庭投入太多,雇主肯定不开心。

第一财经:那你们怎么看待国内出现的“全职爸爸”现象?从本质上说,城市里出现全职爸爸,和《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里提到男性农民工为了生计做出的“男性气质的妥协”,是否一样?
沈洋:我在小红书看到一些“全职爸爸”博主,很多都是要想引流带货,比如有些人带着孩子,一看就是有团队在后面拍。至于说“全职爸爸”的比例,现在没有统计,会不会是个趋势也不好说,但全职爸爸并没有形成一个群体,也没有全职妈妈这么多。
蒋莱:对,“全职爸爸”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男性气质妥协”,因为传统男性气质里没有照料,男性要养家糊口、要掌权。
沈洋:以前我在做农民工研究时,有男性就说,要是在老家就不会洗衣服、做饭,但是在上海,他老婆工作也很忙,两人收入也差不多,他就做“男性气质妥协”,这也是夫妻之间最优的安排。不过,也要看怎么定义“全职爸爸”“全职妈妈”,比如小红书上有些博主说,自己现在当“全职爸爸”一个月的收入是原来的几倍,这其实已经把“全职爸爸”当成工作了。
蒋莱:包括前几年有些育儿公众号,一直打着作者是爸爸的旗号,其实是女性在运作。归根到底还是有性别刻板分工,“全职爸爸”才能够成为新鲜现象,可以吸引眼球,有流量。
“新老人”带来新冲突?
第一财经:你们的“全职爸爸”访谈里,有一个爸爸经历了很多次夫妻之间的激烈磨合后才变得成熟。他说,从小父母只叫他好好读书,没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当一个好爸爸。女孩从小就玩过家家游戏,是不是男性当好爸爸的教育,也应该从小做起来,家庭、学校、社会都要合力?
沈洋:上次我们在茑屋书店做新书分享会,有一个女博士跟我说,她刚生了儿子,让我在她买的书上给儿子签字:“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她会刻意培养儿子更加注重性别平等,我觉得新一代的妈妈是有反思的。
从高等教育入学率来看,2022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生占50.0%,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51.2%,这时不能只是把男性当做标准,让女性去达到,而是女性能做的事情,男性也能做,社会应该对男性也更宽容。
蒋莱:西方发展性别平等文化,往往从幼儿园做起,我们国家要打造生育友好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教育也要从小开始。
第一财经:最近,有学者提出“新老人”这个词,指的是一线城市里,1965~1975年出生的人,他们倾向于摆脱照顾孙辈的责任,认为退休后才是人生开始,更想选择多样化生活,宁愿给子女钱也不想参与孙辈抚养。另一方面,年轻的母亲女性意识越来越觉醒,也注重实现自我价值,试图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保持平衡。那么是否意味着在今后,家庭内部关于是否生育、孩子究竟该谁带的矛盾或者冲突会更加激烈?
蒋莱:这不是冲突,老人也有主体性,有他们的生活。老人不是说就应该帮子女带孩子,子女也不应该对老人有这样的天然期待。“新老人”条件好,能出钱帮衬子女已经挺好了,要不要孩子、要几个孩子还是夫妻两个人的事。
沈洋:所以我们呼唤社会要有托底,有托育服务。最近国家也出台了这样的政策,想打造生育友好性社会,包括有生育补贴、托育服务、灵活就业支持,等等。这些政策都很好,但是我们还希望政策更加有性别视角。比如说,光延长母亲的产假,只会加强劳动力市场对于女性的歧视,还应该要求男性也强制休产假。
蒋莱:对,亲职假在欧盟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亲职假不仅适用于母亲,父亲也有权享受一段时间的亲子照顾假。例如,瑞典的父亲可以享受三个月的育婴假。但是中国、巴西、韩国等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都跟不上,甚至中国社会从上到下还都是一种很卷的职场文化,在家庭、照料、育儿等劳动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亲职文化,尚未得到鼓励。
亲密关系教育从小做起
第一财经:做了这么多访谈,看到那么多婚姻里的困境,你们觉得比较理想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蒋莱:双方都可以自洽,可以好好沟通、协商。双方也都要付出,偶尔会有些退让和妥协,不存在说只以一个人为中心,或者说彼此之间存在上下权力关系,双方之间是平等的、受尊重的。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付出能得到对方的认可。现阶段中国社会,受教育比较好的女性为什么会恐惧进入婚姻?她们看到了什么是理想的婚姻,希望自己也拥有,但没有遇到适合婚恋的人,就对进入婚姻很谨慎。其实这些女性的上一代,也知道理想婚姻是什么,只是她们认为在以前的时代环境下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新型婚姻文化进入社会后,会影响到更多人,大家都想选择能够平等交流和协商的婚姻。因为从恋爱到进入婚姻,再到育儿,增加了大量的工作,也会产生很多矛盾,有种说法不是讲,看起来再美满的婚姻,一生中也有几百万次想掐死对方和想离婚的念头吗?这时都需要夫妇间去寻找解决方案。
沈洋: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家庭是互相尊重,互相认可对方的付出,相互配合,比如一方在事业上升阶段,另外一方就在家务和育儿上做得多一点,反之亦然。在家庭事务分工上,有大家都认可的、比较公平的分配。我们访谈的家庭里,也有夫妻之间做得比较好的,只是因为故事性不够强,最后没有写进去。
蒋莱:其实每个家庭的相处模式不一样,没有所谓好或者幸福的标准。要想有一个性别文化比较好的家庭,就是沈老师讲的,首先还是互相都看到对方,看到对方是人。认为丈夫就是该赚钱,妻子就是该生育,都是没有看到对方是人本身。好的夫妇关系首先应该是友谊关系,大家是人格平等的,可以交流的friendship。在这个基础上,对生活产生共同的向往,决定生孩子还是不生孩子、要生几个孩子、怎么养育孩子,大家都是一起协商、推进的。
现在的90后、00后都觉得,如果没有很强的动力,或者说很爱对方,就不想走进婚姻。我是1979年出生的,我们那时的心理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绝大多数女生都觉得,错过这个好男人就错过了,应该结婚。那时很多人还说,找老公像选绩优股,如果觉得对方没有满足你的期待,就是找了个“垃圾股”,现在想想,也是把对方物化了。过去的教育就是这样,没有鼓励年轻人对爱的理解,觉得婚姻就像一个经济体。如果抱着这样的心理进入婚姻,在婚姻中遇到困难、受挫受阻时,当然觉得非常煎熬和痛苦,因为你没有看到对方,也并不是真的和这个人建立起了亲密连接。
我们还应该对年轻人进行亲密关系教育,这才是上野千鹤子说的真正重要的东西。遗憾的是从小学到大学,这方面的知识学校不教。而在原生家庭里,有人可能又目睹了父母之间质量很差的婚姻,也会影响他们进入婚姻的意愿。所以,社会应该去做推动,让年轻人真的自愿走进亲密关系,实际上人也是有这方面需求的,需要有密切的伴侣;有些人转而去爱宠物,很可能是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失望,寻不到。所以沈老师才在书里说:“家庭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纯粹满足,而是通过不断的冲突与协商之后,有了视家庭为一个整体的‘共产主义’视角,目标是为了家庭及每位成员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