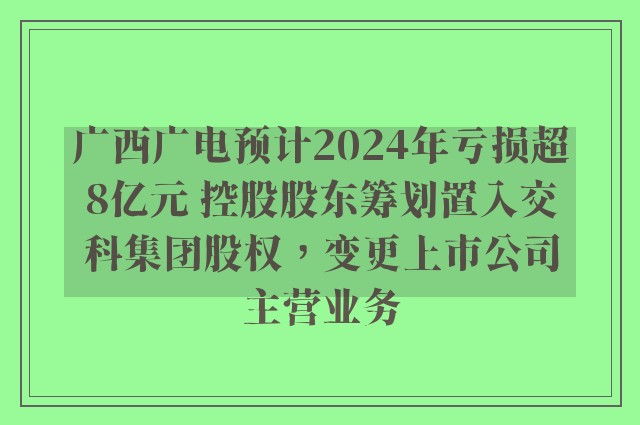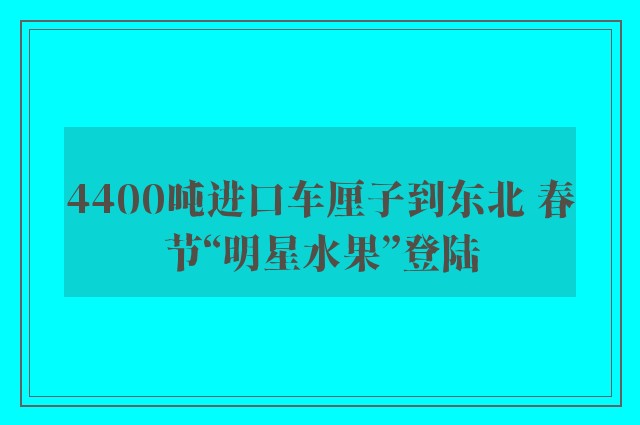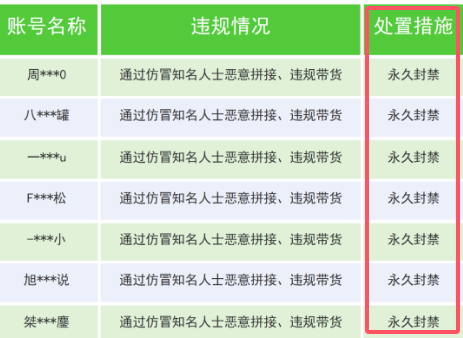从韩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回看过去一个世纪的女性得主
“韩江?谁?”陌生、疑问、到处打听,这就对了,和99%关心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一样,年度获奖者的名字一公布,我也急急忙忙地去打开官方或非官方的信息,看韩江是何许人也。韩国人,女人,写小说的人,1970年生人……
过了5分钟,当有人把中文版《素食者》的pdf发到我所在的微信群里,连带着别人写的几句短评时,我忽然不想关心了。我想到,韩江写的不是一堆pdf,不是一堆epub,她写出的不是一个个手指头碰一下就能打开,再碰一下就能关掉的数字化的文件。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关掉一个正在阅读的作品,或者一段在看作品之前已过眼的短评,然后随口告诉其他人:噢,她就是写××题材的……

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只文学奖是一个“事件”,一个热闹片刻后就鲜有人提的event,而且意味着,“文学”一词本身也成了文学奖的周边,像一个急不可耐的pdf一样,只求人们的“触及”——既然打开它和关闭它都如此轻易。
去年的获奖者,挪威作家约恩·福瑟,当然也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消息一出来,我们的感受是:早该认识他了,早该想到他了,他在戏剧界是如此中流砥柱般的人物,看过他的戏的人如此之多……今年,韩江一获奖,我们马上“熟悉”起来:原来她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的国际认可了,原来她的作品早就得到怎样怎样的高度评价了……这些“早该如此”,都是拜数字技术、互联网传媒技术所赐,我们被蜂拥而至、唾手可得的背景信息淹没,我们被迫“获悉”这个,“获悉”那个,我们不仅(至少自认为)知道了韩江是怎样的作家,而且还知道了她是第18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
“周边”泛滥。我们脑子里被种满了草,我们只是感觉自己“懂”得太多,却没有想到这些拼命想要钻进你脑子里的东西会怎样改变你,比如说,也许会让你抑郁。韩江是个陌生的名字,为此我们被喂以一个个标签,以便认识她,不过,从她的标签,从获奖带出的众多“周边”,也不妨进入若干很有意味的话题。
第18位女性——然后你很快就晓得,这18人中的9人,都是在本世纪头二十三年里获得的,比如2004年的获奖者耶利内克,比如2007年的获奖者多丽丝·莱辛。越晚近越多:从2013年艾丽丝·门罗获奖,到韩江,12年里共有6个女获奖者。这当然说明了变化:女作家(或按照某种更适合扩大传播影响的说法:“女性写作”)“被看见”了,“被重视”了。或许如此。但是,身份政治也成为一个过于突显的事实:“女性”被强调了,此外还有国籍。
在20世纪的100年里,女性获奖者只有区区9个人,而且起码有一半已经被遗忘。谁还会去读1928年的获奖者、挪威小说家温赛特的书?1945年获奖的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她又写过些什么?还有比如1938年获奖的赛珍珠,这个案例,到现在一直被作为诺奖评委们“任性”的证明。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贸然对文学奖表示轻蔑,我们应该看到,在她们的获奖中,在她们的名字被念出时,她们的性别乃至国籍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们是文学写作者,是“文学”领域的人,她们跟男作家一样,都在书写一些全人类的命题和困境。
上世纪的女性诺奖得主们
回看百年前的获奖者时,可见的几乎都是作品,作品中的情节、思想与风格是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时代背景的回应,而作者的诸多身份标签则几乎是不必去注意也不易被注意的。很多作品显得陈旧,以我们今日的习惯难以下咽,然而颁奖的“社会效应”,只需稍多注意,就可以看得清楚。
1909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瑞典人塞尔玛·拉格洛夫,她的《骑鹅历险记》固然如今依然知名,不过,倘若以“儿童/青少年文学”来定义它,就失之简单了。打开这本小说,你可以看到瑞典的壮美山川,可以看到北欧的民间传说,可以读到精心构思的寓言情节,可以看到拉格洛夫对于诸如战争、疾病、道德、儿童等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恳切关心。

《骑鹅历险记》
[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大星文化 2018年4月
拉格洛夫是个堪称博爱的社会活动家。她参与和推动的一些开创性的事业,影响了百年来的世界。比如,她是世纪之交女性和儿童权益保护最积极的推动者,在1900年参与发布了“儿童的世纪”宣言,明言“童年”是每个人人生的一部分,不可以被剥夺,不可以把儿童仅仅看作是成人的预备阶段,而要让儿童有享受童年的权利。这个观点,在《骑鹅历险记》里有再明确不过的表现:尼尔斯的父母就是拿尼尔斯当一个家里的帮工来看待的,根本不知道孩子有他自己的世界。
此外,在20世纪初,欧洲经历了一段难得的“长和平”,拉格洛夫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让和平继续下去,她在书中写了动物运动会的情节,写了一只恶狐狸违反游戏规则,结果被其他狐狸驱逐的情节,这样的构思,是为了呼应现代奥运会的创建理念,即用竞技游戏来促进和平,张扬人类身体的才能,杜绝大规模战争重燃的可能性。
至于1938年的获奖者赛珍珠,她的“时代选择”的属性就更为明显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是西方世界的人文知识分子对东方最为同情、最渴望了解的年代,身为美国人的赛珍珠,写的正是中国农民的故事。如今,早已“过气”的赛珍珠,只是因为身份特殊,她的小说之外的作品,如回忆录和散文,还会受到一些中国出版商的关注,觉得可以往“往事”的角度去做她的书。
然而与拉格洛夫相似,赛珍珠最关注的事务同样是有关“全人类”的。她代表的是跨文化、跨国界的交往、对话的热情,她的游历(虽然常常是被动的搬迁和躲避战火)产生了一种真正的人文视野。
1927年她在南京目睹了暴力事件,随后她又到日本,去体会日本民间的人心,感受其与对外张牙舞爪的军国主义的区别;她在南京的大学宿舍里写出了《美好的地球》;1931年长江水灾,赛珍珠去参加慈善救济活动,写了一系列描述难民困境的短篇小说,这些故事在美国的广播中播出,后来收入她的文集《第一个妻子和其他故事》出版。
在纽约一个由长老会举办的妇女论坛中,出身传教士家庭的赛珍珠说,中国不需要一个由传教士主导的教会,她所见到的传教士们往往是傲慢的,并不真正关心中国普通人的困境。
领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赛珍珠(她当时46岁,非常年轻)彻底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尤其在二战之后“冷战”启幕之时,她为打破东西方之间渐渐树起的坚冰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第一个国际跨种族儿童收养机构就是她在1949年建立起来的;妇女权利、亚洲文化、移民、收养、传教士工作、战争、原子弹、暴力,各种主题都出现在她笔下;当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人普遍屈从于“铁幕”的政治压力时,是赛珍珠,不断依托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公开谈论美国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谈论亚洲战争儿童的困境,想激发公众对国内外受苦之人的注意与同情。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赛珍珠还申请一同前往,然而被无情地拒绝。
赛珍珠的获奖,是为了表彰其作品“为跨越遥远种族界限的人类同情铺平了道路”,这个评语看起来也有点过时,但是,韩江在获奖后拒开任何发布会,并且说知道获奖意味着“承担责任”,这话看起来,至少表面上,很有当年赛珍珠的觉悟。我想,韩江懂得,一旦自己被一堆媒体包围,就必然要回答诸多以“你作为一位女性……”“你作为一个韩国人……”“你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作家……”为开头的提问,她将不得不回应,于是卷入那些琐碎无聊的话题之中,从而不得不在一个身份政治为王的媒介环境里接受“身份识别”。
嘴长在别人身上,标签捏在别人的手里。媒介都有自己的利益,要眼球,要流量,一门心思培养热点和制造话题。清醒睿智的作家,对此是再明白不过的。1996年获奖的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如今,至少在中文阅读的环境里,她算得上是有相当“票房”的外国作家之一,她的若干诗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可以走进大众读者的视野,她被视为智慧、幽默和美兼备的人物。然而,当年在获诺奖之后,辛波斯卡近十年没有写出一本新的诗集。
辛波斯卡也是一位有“世界性”的写作者。回看上个世纪,会发现在大多数的年头,都有真正的“大事”在发生,不说战争、冷战、原子弹和大屠杀,就说1991年,冷战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有时被称为“历史终结”的时期在世人面前展开时,那年的诺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她的作品,同样能使人看到世界上的大事正在哪里发生。那就是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前一年刚刚获释,意味着漫长的种族隔离制度终于看到了一线终结的曙光。南非的种族隔离,当时已被视为人迫害人的一种黑暗象征,就像昔日的柏林墙或奥斯威辛集中营。
戈迪默和拉格洛夫、赛珍珠一样,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在戈迪默的小说里,你并不能轻松地看到清晰的是非对错,看到你想象中的人迫害人的行为,以及对“压迫者”的愤怒讨伐。
戈迪默常常写的是,作为统治者的白人在黑人的“包围”之下的处境,她常常写,那些对自己的特权心怀愧疚的白人,怎样谋求与黑人和睦相处。他们善待黑人,但却无法放弃特权的位置,为此,他们被黑人视为伪善之人。另一方面,在白人和黑人各自的内部,也分裂出各种阵营。戈迪默不仅写出了种族隔离制度之危害,而且告诉她的读者,这种制度并不是可以以一纸法令轻易“废除”的,过去几十年里,一代代南非人心中树立起的看不见的“心墙”,将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
南非在1995年后的历史证明,戈迪默通过小说所发出的凝重的警告是正确的。同样的,柏林墙的倒塌也不能真正弥合墙两边德国人之间的关系。
在其他上世纪的女性得主中,1966年获奖的诗人奈莉·萨克斯,她的诗是与反犹大屠杀的主题直接相关的,在她的沉吟里,针对一个种族的屠杀被提升为人类全体的创伤。而1993年,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瑞森获奖,她的小说,在一个极高的美学水平上将社会中流行的歧视剖露给所有人看。歧视绝非仅仅发生在美国,也绝非仅仅限于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它还缠绕着家庭里的长幼尊卑,缠绕着政治暴力和屈服,反映了人性中的种种普遍暗斑,例如嫉妒、憎恨和傲慢。
上世纪获奖的女作家,总数量多少且不论,就她们做出的贡献来看,其性别身份都不是最主要的。文学涉及所有人,众多的严肃作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公共写作者。文学应该促成对话,凝聚人群,让生活在不同地方、不同处境之下的阅读者,看到彼此之间共有的感受,看到同样的困惑和期待。
21世纪:资讯喧哗与遗忘专家
也许2007年获奖的多丽丝·莱辛,看起来是一位“女”作家,因为她最优秀的作品——发表于1962年的《金色笔记》,是一本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性别是其中突出的主题。然而,莱辛本人有在多个国家、大洲生活的经历,她在前半生中也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国际人士”。即使后期放弃了世界大同的理想,她也没有缩回到性别或者别的什么标签之后。
然而,正如2022年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所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世界上渐渐地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埃尔诺记忆中的世界,是一个“世界上的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的世界,可是新世纪以来,她说,人们都成了短期记忆的能手,成为遗忘的专家。
任何事情——名人逝世也好,局部冲突和战争也好,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也好,政治丑闻也好——统统是一阵“喧哗”。传媒无比地猖獗,第一时间把突发事件推到每个人面前,又冷漠无情地用下一个热点来覆盖它。
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并不是来自这样一个年代。埃尔诺深知(也坦率承认),女性身份、“私生活”写作的性质,为她赢得了当代读者的极大喜爱,但在《悠悠岁月》里,她依然是用一种来自20世纪的社会洞察力,一种对“大时代”的缅怀之心,来描写如今这个年代的热情与空无:
“鼠标在屏幕上迅速轻快地点击,伴着这个节奏,我们总是狂热地想要保住任何唾手可得的照片和图像,但实际上,一旦把它们存到文件夹里,这些文件夹就很难再被打开。”
正因为到处都是被制造的信息和热点,而且人们一般都通过同样的介质——屏幕,或者经由屏幕传出的声音——来获悉它们,所以我们面对一个“新科”(媒体最喜欢用这种词汇)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还想要保持较大的兴趣,就免不了要依靠那些标签、那些周边,要赶快把她的作品储存下来,要在屏幕上看个大概,在获取新知、满足一时好奇的需求背后,我们隐隐地加入“遗忘专家”的大军之中,或者说,加入把一切都变成谈资的大军之中。
打开《素食者》中译本的pdf文件,细读也罢,浏览也好,也很容易产生“小”和“私”的感觉:一个女人选择了素食,为此她受到了各种的不理解、各种的非议。
韩江的笔触里肉身色彩很重,对原始的欲望,对切肤的痛感,她一一秉直写来,似乎也很符合“女性写作”的本分。韩国是个经历过战争和独裁、见证过很多屈辱和政治暴力的国家,比韩江早两辈,有黄皙暎这样的小说家,书写那些大事件下的人心和记忆,而较为年轻的韩江,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避开这些主题的。
可是她的作品依然有可期待之处,因为从《素食者》中已可以看到,韩江把握住了那种自我伤害的微妙心理,它能让人想起那些貌似久远的历史创伤,整个民族的头上都被历史投下了阴影,而民族中传统上的较弱者,例如女性,应当是最有一些“故事”可说的。她们做出的对自己不利的选择,看起来会更具有象征和隐喻性。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可以说,韩江不会是一个只想要贩卖私人题材、性别题材的写作者。
《素食者》的中译本里有一个错误,是非常致命的,必须一提。小说的第二部分,原本是一篇在韩国屡获大奖的中篇小说《蒙古斑》,可是在这个译本里,“蒙古斑”被译作“胎记”。韩国人属蒙古人种,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屁股上都有一个“蒙古斑”,长大之后,大部分人的斑都会消失,在书中,女主角英惠和别人不同,她的蒙古斑一直没有消掉,这隐喻着她身上一直有原始的生命力。然而“胎记”是终生都有的,译作“胎记”,读来不能理解,自然使这个《素食者》译本减去了关键分。

《素食者》
[韩]韩江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磨铁·铁葫芦 2021年9月